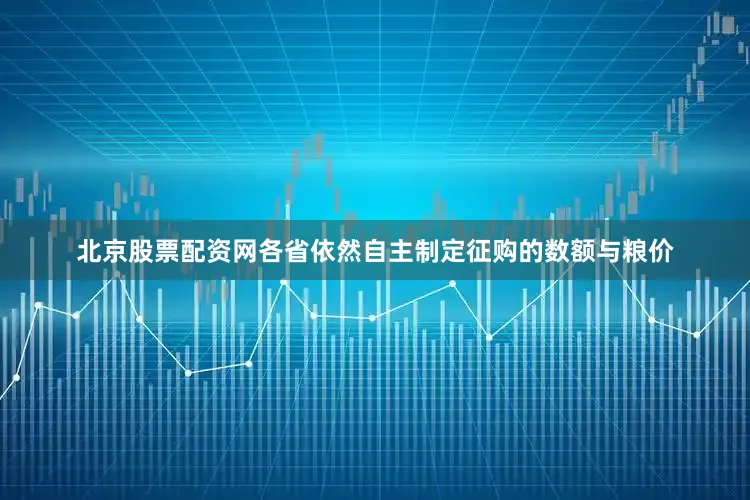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41年7月全面抗战已经持续48个月,国民政府才慢悠悠地成立粮食部,首要任务是保障军队和公务员的粮食供应,同时确保广大民众能以合理价格购得粮食。

由于中央政府过去在南京时期建立的财政基础,多已沦落日本人手中,于是重庆政府必须建立一套新制度,将各省田赋征收权划归中央,并且把田赋征收由法币交税改为征收实物。重庆政府为确保控制一定数量的余粮和遏止通货膨胀,又在1942年宣布向农民定价征购粮食,并由特许的粮食公卖店售予民众。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同时试图加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缩减省政府的独立财政来源,使省县级政府必须高度依赖中央拨款补助。重庆政府同时希望新的田赋征收制度能够加速土地申报和调查工作,废除未经中央许可的强征,并且期望新措施可以让财政收入增长四倍。
一旦此项期望实现后,则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能投入更多资金促进经济建设,切实推行管、教、养、卫等新县制份内的政务。
1、新粮食政策
但是即便是在改制之初,就有中央领袖质疑它的可行性,因为田赋权原本是地方的肥肉,中央把它收归中央而各省的支出改由中央负担,使得县地方自治原本依赖田赋附加者也受到影响。因此四川、云南、贵州等省都产生抵制情绪,咸认为中央集权过甚,而财政部长孔祥熙和粮食部长徐堪都不能说出理由。所以许多领袖们已经预见此一改制前途可能困难重重。
粮食的供应对象应该有三个,分别是军队、公教人员、市场平民百姓。就军队而言,它们的食米部分由中央政府向各省规定每年应该征收粮食的总数,省主席再把总数下达给县政府,然后保甲长从人民手中取得粮食送到县政府,把数据上报给专员公署和省政府。
而省政府再向战区司令官呈交一份各县应该交出的粮食统计单,由战区把粮食分配到各军事单位,并且把各个部队需要粮食数量交给省政府,省政府则命令县政府向附近的军级兵站交出一定数量的食米。照道理说,如果层层依法行事,军队粮食需求就可以顺利满足。
在抗战历经四年之后,新粮食政策标志着重庆中央政府终于试图将治理权力深入到乡村基层,以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直接去管理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
但是如此重大体制改革,并非仅靠意志力和设计,它必须结合政治现实始能生效。重庆方面很快发现,当时国内并不具备推行这一粮食政策的先决条件。政府面临的首要困难便是决定税收标准。此前几代人所经历的长期政治动乱,导致各省地籍资料都混乱不堪或遭战火摧毁。
早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已经普遍存在众多不良现象,包括地籍造假,税率任意提升,税务人员贪污腐败。根据美国人John Lossing Buck教授在1937年调查,虽然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大小地主财产,但是在税册上却没有产权记录。事实上直到1940年12月,全国只有234个县宣称完成土地呈报手续,至于实际到现场去丈量土地去核实土地登记资料的县份则更少。

在1940年代,几乎所有省份的地籍资料仍旧由各地的社书保管,并且也只有社书才能够解读本地地籍资料的含义。正因为如此,纵然新制度在法律上形似赋予中央政府对田赋更大控制权,但它的实际操作仍然必须依赖成千上万的地方原班基层办事人员去划定和征收田赋,和过去情况没有区别。
重庆政府既派不出如此庞大的一支行政和财税队伍下乡直接接管业务,又缺乏足够的组织能力在乡间招募一批新干部去承担这个业务。换言之,重庆政府可以大张旗鼓地制定和颁布政策,但是执行过程仍然操控在原有的地方实力派和传统基层当权派手中。所谓新县制改革只不过把旧酒装进新瓶,完全没有渗透到社会基层。
上述情况为形形色色的非法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比如说,地主和地方旧权势人物可以拒绝呈报土地,或是将大片地产分散登记,以逃避税金或降低税率。保甲长和地方旧权势者沆瀣一气,可以挪用税款,借用民团来强征,随意厘定数额。农民若迟交税款就会被没收其田地,或者处以高额罚款。他们通常还会非法征收附加税等等。饶有趣味的是,战时财政部曾经一度希望伸张社会公平原则,促使富人捐献。
为此还煞有介事地命令地方政府拟造“富力底册”,列举富人资产作为课税依据。但是地方富户豪绅既然把持权力,当然在编造底册时可以隐藏资产逃税,而基层工作人员也迫于威吓或受贿买通而配合造假。一番好意终成画饼。
2、强行征粮的人
战时税收效率肯定和保甲制度有密切关系,因为保甲是中央与地方人民群众接轨的关键和枢纽。
首先的问题是,什么人做保甲长?

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凡是在地方社会稍有地位的人,都不愿意担任保甲长,其原因是保甲长有责任而没有薪俸,办公费极少或是根本不存在。加上地位卑微,事务繁忙,而事务内容又包括征兵、征粮、征工,容易和邻居产生冲突。
因此担任保甲长的人们必须有利可图,而土豪劣绅的爪牙、小地主、无业游民却踊跃为之。他们对于推行重庆政府的政令毫无兴趣,祗图眼前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他们之所以处心积虑争取这些职位,是因为可以乘机中饱、克扣公款等等,值得为之辛劳。虽然他们素质低劣,有的甚至是文盲,然而地方县政府却不得不任用他们,因为只有他们能够以自己的非法手段去完成政府征兵、征粮指标。
即便是传统式乡绅统治方式,在战时大后方某些地区仍然存在,但是重庆政府官吏无法和他们建立直接关系,也钻不进他们那一层长年累积起来的保护壳。尽管地处重庆的国家机构日益臃肿,人浮于事,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却不见踪影,乃至不得不继续依靠地方实力派所掌控的各种组织、人员、规矩、作风,去进行无能无效的抗战事业。
所谓战时动员,无论是人力、财力、或物力,政府在最基层所能依赖的代理人都是保甲长,而这些人绝大部分正是旧社会残余的人物。如果只是赋予他们一些狭小而具体的任务,他们或许可以完成。但是战时的需要是千头万绪,甚至环环相扣,远远超过这些旧社会底层人物的智力和能力,更不必说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地方实力派,而不是个人操守和国家认同感。
因此不禁让人产生出一种感叹,那就是中日战争可以看成是,19世纪落后腐败的中国社会结构和人力资源在和20世纪名列世界前茅的日本军队作战。
以上所描述的这些,来自地方现实状况和地方人士阳奉阴违的手法,都使得政府强制的粮食征购政策难以顺利推行。事实上,各省依然自主制定征购的数额与粮价。中央政府由于缺乏土地调查、呈报与可信统计,也缺乏地方生产与消费量的可靠估算,只能让省政府将其拟定的征购额加诸县政府,而县政府则转嫁到乡、村一级。其结果是,整个系统依然是由地方实力派主导,并且类似1920年代的摊款制度和临时紧急征收手法。
3、新粮食政策失败的原因
干部短缺是新粮食政策推行不力的重大肇因。

重庆政府在1941年推行新粮食政策时,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不到200名干部可供派用。因此政府在1942年不得不加紧训练田赋业务管理专门人才。到了1943年,全国在各级田粮部门供职的工作人员突飞猛进达到175000人,但是其中只有9000人受过短期训练,而且素质高度可疑。
因此仅就执行人才和干部而言,重庆政府的新粮食政策,依然必须仰赖广大后方省份的旧有人员作为推行者,而他们过去曾为军阀征收田赋,既然是原班人马,当然遵循陈规陋习办事。
除人才短缺外,田赋征收的复杂手续同样导致各种不公情形。1941年以前,粮政人员亲自到各村征收田赋,农户以现金缴纳。1941年后,农户却须将沉甸粮食自行设法运送至验收站,并且自负运费。农民通常要自己背负,或租用牲畜,花数日时间才能把粮食从农田运抵验收站。到了验收站,农户还会被粮政人员进行各种刁难,包括借口质量欠佳而拒绝验收,或指责短斤缺两而被迫增加粮量。农民都只好忍气吞声地多交粮食或进行贿赂以求花钱消灾。但是内心肯定极端不满。
粮食收缴之后,下一步是集中运送至储粮设施地点(粮仓)。县政府便会以廉价或无偿方式,强迫农民组成运伕队运输征粮。1941年,大后方省份由于崎岖山地和落后交通,每年收集的粮食平均有三分之二的数额(约4,000万石)需要长距离多次运输,才能送达部队。
而在1942年,全国仅有100辆卡车可供用于粮食运输。1943-1944年间,政府另外组织了400辆木车、900艘木船运送粮食。但这依然无法满足总需求量。无怪乎粮食管理局局长坦承,战时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运输。而运粮又成为农民的严重隐性负担。因为粮政人员非但可以把上级拨交的运费纳入私囊,而且还对于运输规格横加干扰,使人民更痛恨政府与军队,对于1944年河南省军民关系恶化,成为重大因素。
粮食储藏是另一个棘手问题。一则是过去传统政府从未处理过如此庞大的粮食贮藏量任务,二则是传统谷仓在上世纪,就已经被战乱和政局动荡而大量破坏失修。
1938年以后,中国突然面临需要为500-600万军公教人员储备粮食,是过去一两百年来历史上从不曾经历过的负担。1941-1944年间,重庆政府耗尽力气把粮食贮藏量增加了2,600万石,但是实际贮藏量仍然只达到需求量的一半而已。

为了解决储藏问题,政府仓促间被迫转而强征民宅、学校及其他建筑物,将其改造为临时粮仓。粮仓设备的严重缺乏,不仅造成粮食的浪费和损毁,而且为地方官员制造了更多的贪污压榨机会。而在处理这一切问题时,重庆政府既不能仅靠行政命令去推行,也不能使用武力去镇压,只能对地方实力派百般迁就,进行协商谋求合作。
但是对于地方实力派而言,这一切行为都是前所未有,而且来自外界的侵犯,打破了它们的平静生活和行事规矩,损伤了它们的实际权益。即便它们不方便明目张胆地反对“抗战救国”,但是卧榻之上岂容得他人酣睡?因此多方牵制阻扰成为必然结果。
4、发“国难财”的人
在办理粮食征购时,还有些时候是由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收购粮食,其中又仅用一小部分现金去偿付粮价,大多是以政府印造的粮食库券代之,而这些粮食库券又很快便会因通胀而贬值。
各省在决定该年度以何种价格征购多少粮食时,拥有极大自主权。1943年后,有九个省份将粮食“征购”改为粮食“征借”,停止向农户支付粮价,安徽省甚至改为强迫农民“捐献”。
到1944年,所有省份都实施了某种程度的粮食征借。政府为应付战事危急而修改法令,而农民肩上的负担则因此大大增加。中央政府在抗战预算中,历来有一项是列举向农民征购粮食的支出。但是经过中央省县地方等各级官员的层层剥削和贪污之后,这个款项实际上达到农民手中既可以大打折扣,也可以消失无踪。各省情况都不一样。
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一级,粮食部长就被陈诚指责他施压省政府(湖北)降低收购农民粮食的价格,其目的则是方便政府官员可以在市场以高价抛售,而部长个人则中饱大批粮款存入川康银行,“发国难财”。
而在重庆政府预算的征购粮食价格中,对河南省的拨款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前已经超过9亿元,但是人民并未得到粮款,也不知中途被何人吞没,但是肯定导致政府信用大受打击。至于个别官吏借征粮而进行贪污,则在全国各地更是层出不穷。

比如说,浙江省一个县长被军风纪巡查团查获,在1943年办理粮政舞弊,贪污至七,八百万元。1943年一个大案惊动了蒋介石。河南省粮食管理局局长先是挪用公款一百万元获利后,又挪用公款五百万元。蒋介石震怒之余,以手谕指示军法总监部立案彻查。
相对于内地省份的县乡政府,以征收征购和征借粮食去进行贪腐,在前线通常是军队抢在日军和伪军之前征集余粮。大多数情况下,名为征购,实则是赤裸裸的抢夺。
5、农民日渐加重的负担
回顾制定新粮食政策的初意,本为同时满足军队、公务员和广大民众的需求,但实施结果远不能达到理想目标。1940年代,通过田赋征实征得的粮食数额根本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还须征购粮食作补充。就公务员而言,重庆的中央级公务员有一定的粮食配额,在外地的中央干部和多数省级公务员则只有粮食补贴,而补贴又完全跟不上不断疯涨的粮价。
此外,战时粮食政策还使省县政府的预算大幅降低。例如,1941年浙江获批准的省预算仅为1937年的1/13,县预算仅为战前的1/6。
地方政府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只好向人民征收附加税,而弱势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阻止。例如在1942年,除全国粮食征实征购8,000万石外,县级单位还另外征收公粮2,000万石左右,占全国公粮的1/4。
至于一般社会上消费者,其粮食需求量大,但是政府未能控制足量余粮和实行全面价格管制,其结果是,城镇居民只能任由屯粮的商人和飞涨的物价摆布。
如果不把粮食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考察,我们就难以理解重庆政府在战时粮食政策上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战前粮食市场供应,取决于粮食生产量与人口消费量之间的平衡。
南京政府战前产粮统计资料显示,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是全国产粮最多的省份,经常有余粮可供输出的省份则是江苏、湖南、和安徽。至于四川与浙江两省则偶尔输出粮食。其余各省或则缺粮,或则仅供自足。但是到了战争后期,状况全然改变。1941年,在没有被日军占领的省份如四川、云南、湖南、广西、河南、山西等这一大片区域中,只有四川和湖南仍有余粮。打破平衡的崭新因素,是军队和战事。
如果回顾1920年代北洋军阀鼎盛之时,全国也只不过供养了200-250万军队。但是到了1940年代,国统区的粮食总产量已经低于战前的一半,却要供应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大约450-500万士兵),同时还要维持连年不断的军事活动,特别是日军惯常在秋季收成期间进行抢粮战争,其强度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属于罕见。

这些前线战事和掠夺,使得后方非沦陷区省份的老百姓负担相形加重。其中尤以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老百姓负担最重,而且逐年增加。在战前,这四个省份的粮食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2%,到1941年这四个省份提供的公粮已占全国征实征购粮食的31.5%。到了1941-1945年间,仅仅是四川省一个省份缴纳的公粮就达全国总量的31.6%。
尽管官方统计显示的粮食征实、征购数额仅占国统区粮食总产量的5%-6%,但农户的实际负担应该远高于此。如果算上所有非法的勒索搜刮抢夺,甚至可能超过10%。考虑到多数农民在承平时代也仅能维持糊口的生活水平,这一战时负担会造成他们生存资源的严重损失。
更糟糕的是,战争负担并非对所有人平均分配。贫苦农民被剥夺生计,而富裕农民和地主不仅逃避赋税,而且经常囤积粮食谋取暴利。毫不奇怪地,战时粮食政策刚开始推行,内地省份便出现农民暴动。

1942-1943年间,包括贵州、青海、宁夏、甘肃,甚至四川都曾发生动乱,有时多达5万多名武装农民参与,抗议政府赋税制度的腐败与暴虐。甚至曾有省或地方保安团擅离职守,加入农民暴动行列。随着时间流逝,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些省份的农民开始结帮成匪与官兵对抗,造成土匪数量明显增长。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图文带货训练营#
博星优配-炒股资金配资-正规的股票配资公司-国内十大配资平台排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